[电影] 《狂野时代》:这部"元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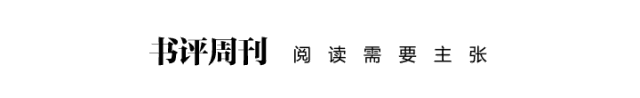
近日,电影《狂野时代》上映,口碑引发两极争议。喜欢的观众惊叹于它奇崛的想象力;不喜欢的观众则认为是浪费时间。如何理解这部有些不一样的院线电影?
自2015年《路边野餐》横空出世,来自贵州凯里的年轻人毕赣便成为备受国内外电影界关注的作者导演。充满诗性的视听美学、阴郁潮湿的气质、鬼魅混沌的时空,该片展露的种种特质让众多影迷、学者迫不及待地将其放置于苏联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诗电影”的坐标系中(毕赣本人也是塔可夫斯基的拥趸)。2018年底,毕赣推出了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获得巨额投资、制作成本翻倍的电影既承接了毕赣对于时间和梦境的探索,也延续了其超现实的风格化表达。然而,将“一吻跨年”作为核心营销卖点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一经上映便被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淹没,口碑和票房急转直下。当毕赣不得不直面大量不属于自己作品的观众时,他的困境与无奈才得到真正地显现。
时隔七年,毕赣携新片《狂野时代》来到了第7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这部由易烊千玺、李庚希、舒淇、赵又廷、黄觉等一众明星出演的作品将主角设置为“电影怪兽”,似有穷尽电影之本真的野心。国际奖项的认可难掩主流院线的失落,尽管《狂野时代》在个人表达上做出了诸多调整甚或妥协,但此片在国内的两极化口碑仍未改变艺术影片在电影市场的尴尬处境。与此同时,评论界对于毕赣创作力退化的批评声也愈加尖锐,也许,相较于如何收获更多影迷,毕赣如今面临的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留住曾经的观众。
撰文|回答
在时间中游荡
毕赣的电影母题
相信最初与《路边野餐》产生共鸣的观众,无一不被其情感、记忆、梦境的稠密和混杂打动。专注于对时间本体的探索与表达是毕赣电影最具作者性的体现。从具象化的表盘、轮胎、火车、瀑布,到以圆周为轨迹的镜头运动,再到人物超出现实逻辑的遭遇,在时间一层层的拆解与重塑中,毕赣创造了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于同一平面共处、交织、缠绕的场域。毕赣作品的时间观念源于《金刚经》里的三句话:“现在之心不可得,过去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即时间难以被精确记录,也不能被清晰划分,如一条首尾相连、绵延流动的河流。

《路边野餐》电影剧照。
在《路边野餐》虚构的河畔小镇荡麦,毕赣用一段42分钟的长镜头表现了主人公陈升与亡妻、侄子等人的相遇,他们处在与陈升相对的过往、当下和未来,却在一个完整的镜头里悉数出现,与陈升的生命产生宿命般的交织。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长镜头经常被用来记录完整的物理时间,而毕赣却在一个镜头里创造超维的时间轴,让时间挣脱物质现实的约束。在这个兼具现实感与奇幻感的时空里,陈升由寻找他人转为与自我相逢,影片的情感张力与内在情绪不断翻腾,物理时空发生的事件越失真,角色的内心情感就越深沉。而对于影片里的人物来说,只有成为自由绵延的时间的一部分,才能挣脱时间的囚笼。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更多... |
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