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學者呼吁:不能繼續讓精神病成為"免死金牌"
8月10日,南昌市青雲譜區青雲譜路附近發生壹起傷人案件,19歲女大學生與朋友旅游時,遭壹名男子捅刺多刀身亡。
8月12日,南昌市公安局青雲譜分局發布通報稱,犯罪嫌疑人席某某今年23歲,有精神疾病診療史,已被刑事拘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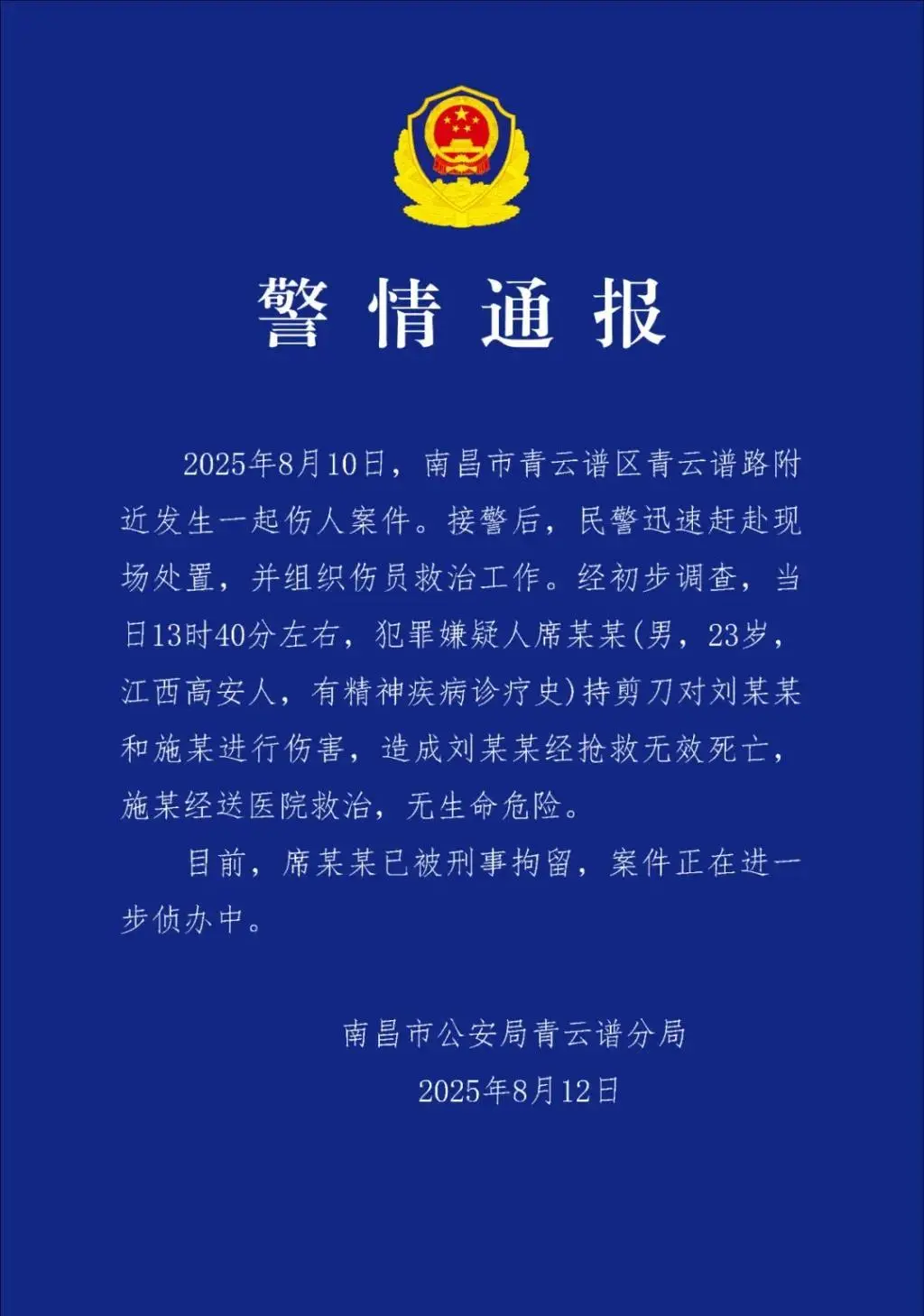
花樣女孩無辜遭遇不幸,嫌疑人有精神病史,這些信息再次沖擊公眾神經,大家在對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同情的同時,也對精神病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表達了壓倒性的支持態度。
類似的案件不是個例,每隔壹段時間我們都要拷問壹遍:“為什麼精神病人就不需要承擔責任?”“如果他不承擔責任,那麼誰來承擔責任?”
對於“精神病人患者也應該承擔刑事責任”這壹觀點,很多法學理論工作者都表達了謹慎的反對觀點,甚至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支持‘精神病人行凶壹律入刑’帶來的是虛幻的安全感”。
但問題是,支持“精神病人行凶壹律入刑”這種樸素法感情的第壹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安全感嗎?是為了以後自己可以不被精神病人行凶嗎?不說大錯特錯,但至少重點放錯了地方!
刑罰作為壹種特殊的“公益訴訟”,第壹目的是為了實現群眾對於合法權益受損之後的刑罰期待,這種期待優位於刑罰的教育效果。換言之,“殺人償命”背後的邏輯從來不是如果不償命,那麼就會有人也來殺我,而是殺了人必須“以命抵命”這種最為樸素的法益平衡。而殺人償命後同時會對其他潛在的殺人沖動帶來抑制效果,當然也是刑法所期待的,卻並不是壹個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的法律效果。畢竟死刑廢除論者往往都是用死刑並不當然會抑制犯罪來做論證的。
對於精神病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並不是壹個所謂的主觀和客觀這種要件層面的問題,而是壹個責任減輕或免除角度的問題,類似於民事責任情形下討論違法阻卻事由中的事項,年齡、精神狀態、正當防衛等等均屬於這壹領域內的事項。
換句話說,在這類違法阻卻事由的討論中,並不是論證是不是明知、故意實施了刑事犯罪亦或者民事侵權,而是當構成要件論證完成之後,出現了法定的阻卻從構成要件走向法律效果這壹法律推論的事項。
因此,對於精神病人無須或者減輕刑事責任的論證邏輯,其實並不在於很多學者所謂的其並不具備犯罪的故意或者過失,而在於其並不理解其所實施的行為所可能帶來的法律效果評價,這兩句並不能簡單地做並列對待。換言之,主觀要件更多地應該評價行為人(無論其是否精神正常)是否知道其正在為的行為,而不是其正在為的行為會帶來何種法律效果。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違法性阻卻事由在精神病人以及未成年人犯罪上就會形成統壹的判斷標准了,兩者並不是不知道自己實施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行為,而是他們都不知道這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會帶來何種法效果。於是減輕和免除的標准也就來到:我們應該如何期待他們在何種犯罪中達到何種認識上?
在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爭論和實踐中,為何在特定幾類案件中能夠下降年齡標准,更多的是在法治教育發展的現狀、具體實踐數據的總結,以及民眾的接受程度相輔相成之後科學又民主的產物。尤其對民主的重要度,在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無論其在整個論證過程中如何科學嚴謹,最終都必須經過民主決策的把關。不是所有符合科學的就壹定都體現為法律,要允許民眾對於科學的忌憚和擔憂。
因此,立法的核心可以理解為:科學論證、學者觀點都屬於重要的條件,但真正意義的必要條件還是民主決策。換個接地氣壹點的表達就是:不管科學上如何如何肯定、學者們如何如何贊許,倘若當前民眾社會基礎無法達成壹致,那這個立法也很難說是壹個必須且完美的立法。而反過來則應當表達為,對某個立法,無論當前民眾社會基礎多麼多麼壹致,這個立法也必須經過科學上的論證、各地試點等實踐經驗的積累之類才能出台。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8月12日,南昌市公安局青雲譜分局發布通報稱,犯罪嫌疑人席某某今年23歲,有精神疾病診療史,已被刑事拘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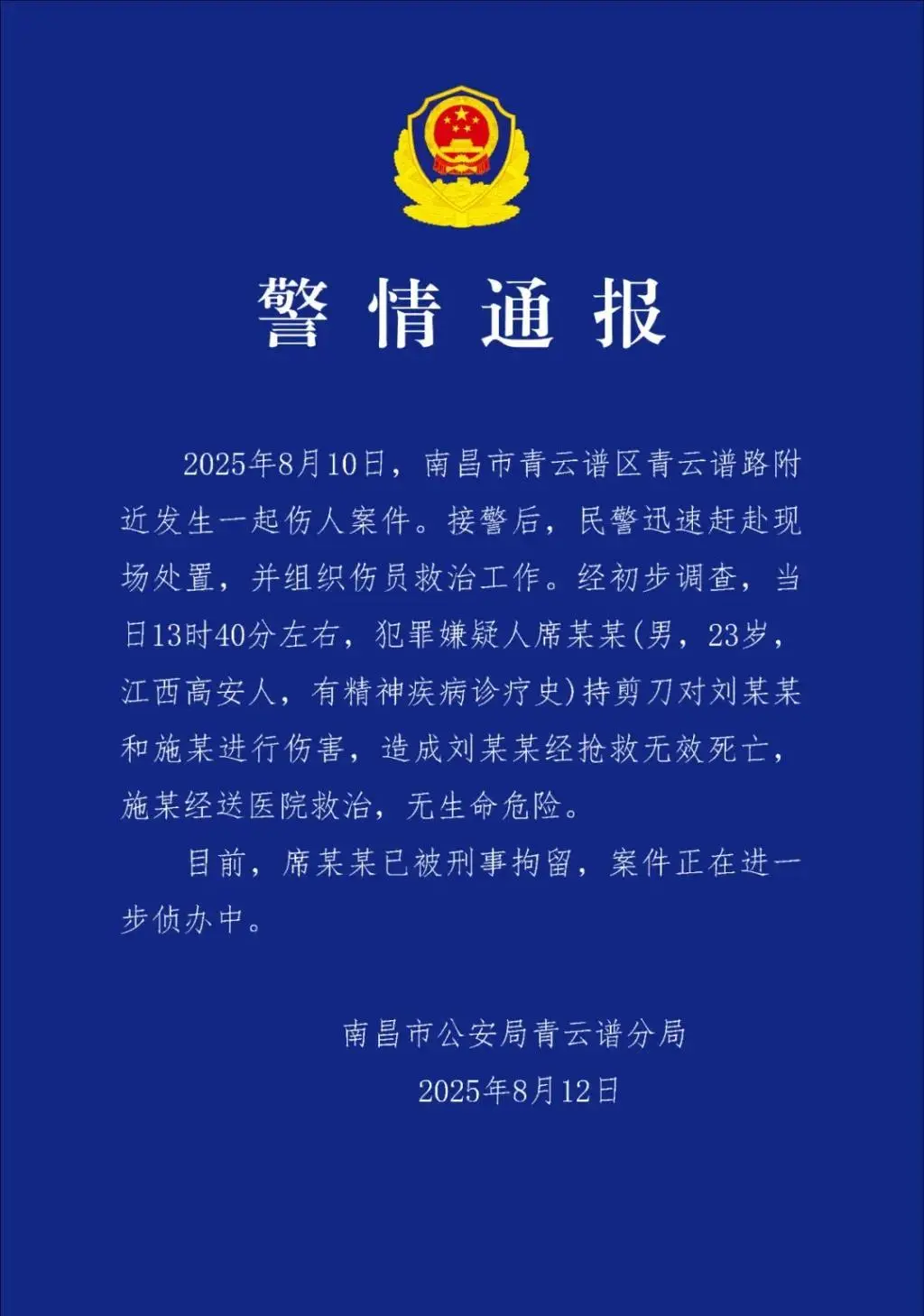
花樣女孩無辜遭遇不幸,嫌疑人有精神病史,這些信息再次沖擊公眾神經,大家在對被害人及其家屬表示同情的同時,也對精神病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表達了壓倒性的支持態度。
類似的案件不是個例,每隔壹段時間我們都要拷問壹遍:“為什麼精神病人就不需要承擔責任?”“如果他不承擔責任,那麼誰來承擔責任?”
對於“精神病人患者也應該承擔刑事責任”這壹觀點,很多法學理論工作者都表達了謹慎的反對觀點,甚至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支持‘精神病人行凶壹律入刑’帶來的是虛幻的安全感”。
但問題是,支持“精神病人行凶壹律入刑”這種樸素法感情的第壹目的是什麼?是為了安全感嗎?是為了以後自己可以不被精神病人行凶嗎?不說大錯特錯,但至少重點放錯了地方!
刑罰作為壹種特殊的“公益訴訟”,第壹目的是為了實現群眾對於合法權益受損之後的刑罰期待,這種期待優位於刑罰的教育效果。換言之,“殺人償命”背後的邏輯從來不是如果不償命,那麼就會有人也來殺我,而是殺了人必須“以命抵命”這種最為樸素的法益平衡。而殺人償命後同時會對其他潛在的殺人沖動帶來抑制效果,當然也是刑法所期待的,卻並不是壹個存在直接因果關系的法律效果。畢竟死刑廢除論者往往都是用死刑並不當然會抑制犯罪來做論證的。
對於精神病人無需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並不是壹個所謂的主觀和客觀這種要件層面的問題,而是壹個責任減輕或免除角度的問題,類似於民事責任情形下討論違法阻卻事由中的事項,年齡、精神狀態、正當防衛等等均屬於這壹領域內的事項。
換句話說,在這類違法阻卻事由的討論中,並不是論證是不是明知、故意實施了刑事犯罪亦或者民事侵權,而是當構成要件論證完成之後,出現了法定的阻卻從構成要件走向法律效果這壹法律推論的事項。
因此,對於精神病人無須或者減輕刑事責任的論證邏輯,其實並不在於很多學者所謂的其並不具備犯罪的故意或者過失,而在於其並不理解其所實施的行為所可能帶來的法律效果評價,這兩句並不能簡單地做並列對待。換言之,主觀要件更多地應該評價行為人(無論其是否精神正常)是否知道其正在為的行為,而不是其正在為的行為會帶來何種法律效果。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違法性阻卻事由在精神病人以及未成年人犯罪上就會形成統壹的判斷標准了,兩者並不是不知道自己實施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行為,而是他們都不知道這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會帶來何種法效果。於是減輕和免除的標准也就來到:我們應該如何期待他們在何種犯罪中達到何種認識上?
在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爭論和實踐中,為何在特定幾類案件中能夠下降年齡標准,更多的是在法治教育發展的現狀、具體實踐數據的總結,以及民眾的接受程度相輔相成之後科學又民主的產物。尤其對民主的重要度,在這裡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法律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無論其在整個論證過程中如何科學嚴謹,最終都必須經過民主決策的把關。不是所有符合科學的就壹定都體現為法律,要允許民眾對於科學的忌憚和擔憂。
因此,立法的核心可以理解為:科學論證、學者觀點都屬於重要的條件,但真正意義的必要條件還是民主決策。換個接地氣壹點的表達就是:不管科學上如何如何肯定、學者們如何如何贊許,倘若當前民眾社會基礎無法達成壹致,那這個立法也很難說是壹個必須且完美的立法。而反過來則應當表達為,對某個立法,無論當前民眾社會基礎多麼多麼壹致,這個立法也必須經過科學上的論證、各地試點等實踐經驗的積累之類才能出台。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