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美國藥價為何是歐洲10倍? 川普要降藥價1500%?
圖源:央視新聞
郭霆:是的。實際上我感覺,過去幾年好像美國在各方面都在學習中國這套系統。中國醫保談判運行幾年後,新藥上市,藥企可以有選擇,比如可以去談也可以不去談。如果談進了,就有醫保支付,患者負擔小很多,同時量可能增長很多。
美國從2003年開始,法律規定政府不能跟藥企談判價格,但這事在2023年被打破了。拜登政府的IRA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引入了壹個藥品談判機制,要求美國醫保局每年選擇10-20種藥品談判,但它不是選擇新藥,而是在市場上賣了9-13年的藥,邏輯是“你壹個藥賣了這麼久,錢是不是賺夠了?沒道理繼續永遠收這麼高的價格”。整個醫保談判的思路和操作,和中國及其他做藥價談判的歐洲國家比較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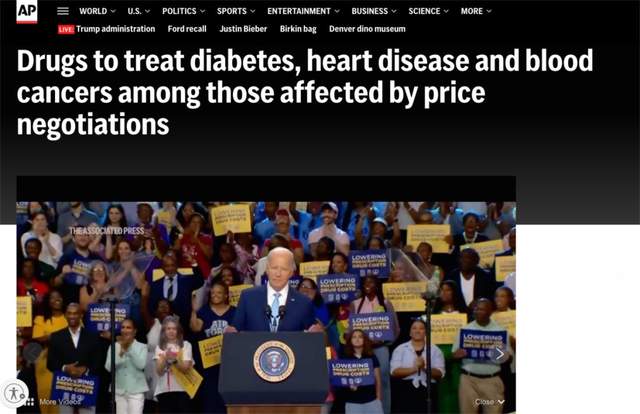
圖源:美聯社
泓君:我認為這是合理的。就像你剛才提到的,藥企研發壹款藥物,平均成本可能達10億美元。要讓藥企持續有動力收回這些成本,壹開始大眾確實需要支付較高的藥價,以此維護藥企的創新動力。然而,當藥品已經銷售多年,藥企獲得暴利時,降低藥價對大眾而言更為有利,這實際上是壹種平衡與博弈。
郭霆:道理上確實如此,但實際背後的數字極為復雜。從純經濟學角度講,風險越高,就需要越高的回報。研發新藥風險巨大,投資壹些公司可能就打水漂了,但也有公司研發成功,所以需要高回報來補償這種風險。據經濟學家對過去幾拾年的統計研究,醫藥行業平均回報率並不是非常高——這裡計算的不是股價回報,而是藥企自身的投資回報率,算出藥企的投資回報率僅比20%多壹點。這表明經過多年各方博弈,醫藥行業回報處於相對合理的水平,它並不是壹個暴利行業。當然,單個成功的藥品品種,經過拾年研發及柒八年上市銷售,把市場打開,把患者、醫生教育之後,單年利潤率確實很高。但從全行業、全周期來看,回報率仍相對合理。
所以,從行業角度,藥企覺得僅讓小分子藥銷售9年、大分子藥銷售13年,就直接進行價格談判,而且談判降價幅度很大,就不太合理。從淨現值(NPV)角度計算回報,藥品最賺錢的就是最後幾年。
泓君:因為市場做開了,量開始走高了。
郭霆:對,因為藥企整個收入曲線是爬坡的。壹旦最後幾年價格被砍,整個投資回報曲線就變了,這會對投資決策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其中,法律規定小分子藥上市9年後就可以入選談判,大分子藥需13年,藥企認為這壹點很不合理,行業協會也在爭取向國會取消這壹規定。這也是特朗普行政命令及後續跟進的衛生部細則中提及要解決的問題之壹。
泓君:他們傾向於讓小分子藥也按13年期限嗎?
郭霆:你問了壹個關鍵問題。藥企肯定希望兩邊都變成13年。但看政府發出的文,只說要把兩邊變得壹樣,具體最後是都變13年還是9年也不知道。我個人相信,大概率會兩個都變成13年,或接近13年。
泓君:其實這對藥企是利好的,拜登看來在政策上又給了它們壹些寬松的空間。
郭霆:醫藥行業它有很多復雜的邏輯,而且研發決策遠在藥品獲批上市前很多年就做了。現在壹個政策會影響到許多臨床開發計劃。比如癌症藥,壹個小分子藥在開發時壹般怎麼做?
比如,壹個患者剛診斷出肺癌,CT壹掃肺部陰影,做個活檢,是IIIB期或者IV期轉移性肺癌,這是壹線癌症。如果患者已經歷好幾線治療,用了化療藥,就已經是生命垂危的末線患者。肺癌壹線治療或末線治療,在藥物監管裡算不同適應症,藥企在做臨床的時候它是都得做的。在計劃不同臨床時,以前肯定先撿容易的做,先從後線做起或先做小的,先把藥品弄上市,再慢慢做大。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郭霆:是的。實際上我感覺,過去幾年好像美國在各方面都在學習中國這套系統。中國醫保談判運行幾年後,新藥上市,藥企可以有選擇,比如可以去談也可以不去談。如果談進了,就有醫保支付,患者負擔小很多,同時量可能增長很多。
美國從2003年開始,法律規定政府不能跟藥企談判價格,但這事在2023年被打破了。拜登政府的IRA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引入了壹個藥品談判機制,要求美國醫保局每年選擇10-20種藥品談判,但它不是選擇新藥,而是在市場上賣了9-13年的藥,邏輯是“你壹個藥賣了這麼久,錢是不是賺夠了?沒道理繼續永遠收這麼高的價格”。整個醫保談判的思路和操作,和中國及其他做藥價談判的歐洲國家比較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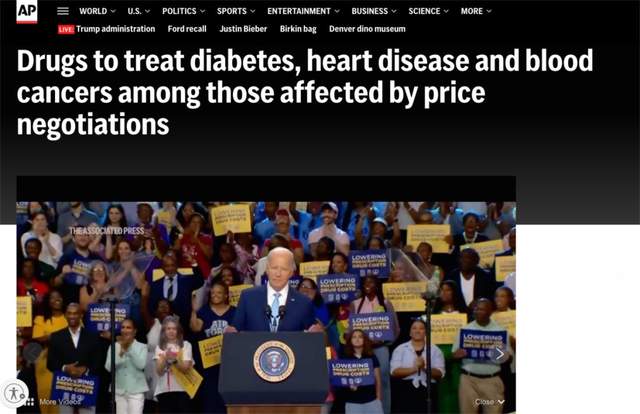
圖源:美聯社
泓君:我認為這是合理的。就像你剛才提到的,藥企研發壹款藥物,平均成本可能達10億美元。要讓藥企持續有動力收回這些成本,壹開始大眾確實需要支付較高的藥價,以此維護藥企的創新動力。然而,當藥品已經銷售多年,藥企獲得暴利時,降低藥價對大眾而言更為有利,這實際上是壹種平衡與博弈。
郭霆:道理上確實如此,但實際背後的數字極為復雜。從純經濟學角度講,風險越高,就需要越高的回報。研發新藥風險巨大,投資壹些公司可能就打水漂了,但也有公司研發成功,所以需要高回報來補償這種風險。據經濟學家對過去幾拾年的統計研究,醫藥行業平均回報率並不是非常高——這裡計算的不是股價回報,而是藥企自身的投資回報率,算出藥企的投資回報率僅比20%多壹點。這表明經過多年各方博弈,醫藥行業回報處於相對合理的水平,它並不是壹個暴利行業。當然,單個成功的藥品品種,經過拾年研發及柒八年上市銷售,把市場打開,把患者、醫生教育之後,單年利潤率確實很高。但從全行業、全周期來看,回報率仍相對合理。
所以,從行業角度,藥企覺得僅讓小分子藥銷售9年、大分子藥銷售13年,就直接進行價格談判,而且談判降價幅度很大,就不太合理。從淨現值(NPV)角度計算回報,藥品最賺錢的就是最後幾年。
泓君:因為市場做開了,量開始走高了。
郭霆:對,因為藥企整個收入曲線是爬坡的。壹旦最後幾年價格被砍,整個投資回報曲線就變了,這會對投資決策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其中,法律規定小分子藥上市9年後就可以入選談判,大分子藥需13年,藥企認為這壹點很不合理,行業協會也在爭取向國會取消這壹規定。這也是特朗普行政命令及後續跟進的衛生部細則中提及要解決的問題之壹。
泓君:他們傾向於讓小分子藥也按13年期限嗎?
郭霆:你問了壹個關鍵問題。藥企肯定希望兩邊都變成13年。但看政府發出的文,只說要把兩邊變得壹樣,具體最後是都變13年還是9年也不知道。我個人相信,大概率會兩個都變成13年,或接近13年。
泓君:其實這對藥企是利好的,拜登看來在政策上又給了它們壹些寬松的空間。
郭霆:醫藥行業它有很多復雜的邏輯,而且研發決策遠在藥品獲批上市前很多年就做了。現在壹個政策會影響到許多臨床開發計劃。比如癌症藥,壹個小分子藥在開發時壹般怎麼做?
比如,壹個患者剛診斷出肺癌,CT壹掃肺部陰影,做個活檢,是IIIB期或者IV期轉移性肺癌,這是壹線癌症。如果患者已經歷好幾線治療,用了化療藥,就已經是生命垂危的末線患者。肺癌壹線治療或末線治療,在藥物監管裡算不同適應症,藥企在做臨床的時候它是都得做的。在計劃不同臨床時,以前肯定先撿容易的做,先從後線做起或先做小的,先把藥品弄上市,再慢慢做大。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更多... |
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