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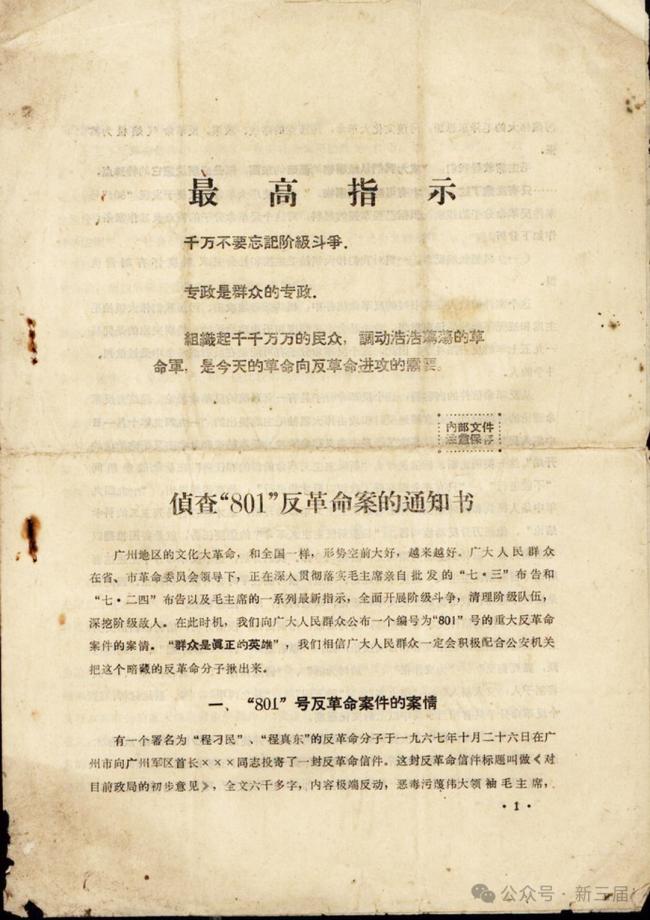
第二天,我学校的对立派两个学生跑到我家,在家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警告我们,要划清界线,只许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一时引来众多街坊围观。
1968年10月,学校通知我们返校,那天,教学楼上还挂着残存的大标语,上面斗大的字:“赵某某对抗运动,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我的母校“广州建联中学”,是父亲供职的广州市第五中学“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所在地)。学校里进驻了“工人宣传队”,是动员我们“上山下乡”的。
从1966年6月开始,全国学生“停课闹革命”,至1968年,这两年里没有招生,也没有学生毕业,普通中学滞留了三届学生,即现在俗称的“老三届”,指的是66、67和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合起来是六届。经过一番动员,初中生除了部分家庭成分“好”的,个人表现佳的继续升学,高中生极少数留校当“辅导员”外,其余全部要“上山下乡”。我的班五十多人,除了一人当“辅导员”外,几乎都去了农场或下农村插队落户。
我因患肺病,医生证明上写着“不宜参加体力劳动”而暂时得以留城。到了1969年初,上级下发通知:因各种原因滞留城市未下乡的中学生的档案全部拨归居住地所属街道,以后由街道组织继续动员;因家庭生活困难的(如父母年老体弱,又是独生子女),或身体状况不适宜下乡者,由街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我的“上级 ”改为街道派出所,我的关系转到了居委会,而居委小组长成了我的直接“上级”。
1968年12月“复课闹革命”,部分获得升学资格的“老三届”初中生直接升上了高中,我的三妹是小学六年级应届毕业生,亦直接递升读初中三年级,所以,她从来没有读过初一和初二。小妹小学三年级,直升为六年级,可谓“连升三级”。
“有病就得安心养病,其他什么都不要去想了。”当时母亲含着泪对我说。我只有默默地点头。然而,此心如何能“安”得下来?
父亲死后理所当然地停发了工资,现在是母亲的一份工资需养活四个人,还得每月抽出10元让我去医院开药打针,更遑论家中负了的债务(父亲死时的火化费60元全由家属支付)。家庭经济的压力让母亲艰难地扛着,我曾寄希望于街道能安排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哪怕每月15—18元,我一定感恩不尽。
后来才明白,我的这一厢情愿其实是在做白日梦,上级早就将我们一家打入了“另册”——现行反革命的子女还想在城市里工作?之后,每当有动员街道青年下乡,我是必被通知的一员,就算是我出示了医生证明也不能豁免。在他们眼中,我是必须去农村接受改造的,甚至有居委的干部这样“劝说”我:农村空气好,食物新鲜,你先下去养病,病好了以后再参加农业劳动。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
那几年里,我们一家人难得添置一件衣服,两个小妹才十来岁,为了让她俩过年穿上一件新衣裳,母亲竟然常年不吃早餐,每日省下几分钱,积上好久,才去扯几尺布,请人缝制新衣。我们的衣裤破了,总是补了再补。
一位街坊我们喊她梁大姐的,她的丈夫亦在文革中自杀,与我的母亲遭遇一样,于是她们同病相怜。梁大姐以替街坊修改、缝补衣服为生,家中有缝纫机,我母亲常常在夜晚拿着我们的衣服去缝补。
家里各人洗澡都是用洗衣皂,因为买不起香皂。我还记得母亲的洗脸毛巾都快破成渔网了,还是舍不得买新的,每天洗脸时是拿着揉成一团的毛巾往脸上涂擦。
要说经济困难,生活艰辛,总还不至于饿饭,能熬得过去,更难以忍受的是我们还处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时时刻刻都处于恐惧之中。
居委会的干部常来通知你去开会学习,不厌其烦地、不断地动员我去下乡,大凡开批斗会(斗争“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等)必定叫我去参加,坐在被特定安排的位置上,让群众一眼就看出我们是“另类”。
还有更恶劣的是半夜里来查户口,凌晨一时许,到家来拍门,一家人在睡梦中被惊醒,大门打开,为首者是穿着制服的警察,他带领着居委会的干部老太太,还有手执水火棒的年轻的街道积极分子,一窝蜂地涌进家里来。
警察说,现在查户口,把我们家的户口本打开,煞有介事地对照家庭人口,问家中有没有外人留宿。其时,居委会老太太已在屋内到处窜,手拿电筒乱照,还查看床底下有否藏匿着什么人。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涉嫌参与2012年恐袭班加西美领馆嫌犯被引渡至美 涉嫌参与2012年恐袭班加西美领馆嫌犯被引渡至美 |
 巴基斯坦首都爆炸已致31死 初判为"自杀式恐怖袭击" 巴基斯坦首都爆炸已致31死 初判为"自杀式恐怖袭击" |
 父亲去世后存款,儿子想取需先证明"我爸是我爸"? 父亲去世后存款,儿子想取需先证明"我爸是我爸"? |
 加州州长纽森谈母亲协助自杀经历:我曾恨她让... 加州州长纽森谈母亲协助自杀经历:我曾恨她让... |
 淫魔爱泼斯坦狱中自杀 死亡现场首度曝光 淫魔爱泼斯坦狱中自杀 死亡现场首度曝光 |
 砸车偷卡还洗钱?BC省府拟嫌犯车辆 砸车偷卡还洗钱?BC省府拟嫌犯车辆 |
 被当作"孵化器",爱泼斯坦案未成年女性日记曝光 被当作"孵化器",爱泼斯坦案未成年女性日记曝光 |
 藏在文字里的暖意:洪晃与父亲洪君彦 藏在文字里的暖意:洪晃与父亲洪君彦 |
 妻失踪加国华裔被枪杀 7嫌犯被捕 妻失踪加国华裔被枪杀 7嫌犯被捕 |
推荐:
 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
父亲自杀后, 我被当作"特一号"案嫌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