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淇《女孩》:写给青春的散文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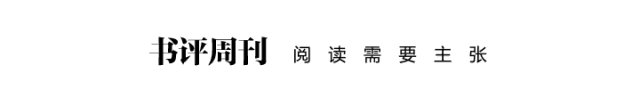
演员舒淇自编自导、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的电影《女孩》,虽然助其一鸣惊人,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在第3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斩获最佳导演,但是,自11月上映以来,该片迄今票房仍未突破500万。豆瓣开分亦是无功无过的7.2,评论两极分化,有人说情节平淡破碎,观影堪称折磨,有人指戳中青春心事,看得泪流满面。无论从叫好还是叫座角度,相较“女性成长”的市场大势,叠加“大女主”舒淇跨界首执导筒的噱头,《女孩》的曲高和寡,确实不似预期。
但这一切显得既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舒淇屡次在访谈中坦承,“做导演完全是侯导叫我拍”。2009年,侯孝贤已建议她“试试做导演,写自己的故事”,惟说者有意听者无心,参演《聂隐娘》之际,侯导再度殷殷叮咛,舒淇才有意识地“从最熟悉、最想表达的内容开始”,正式筹备剧本。
其实,作为出道30年的女演员,舒淇“自己的故事”,关于酗酒的父亲、18岁生下她“小孩带小小孩”的母亲,早早在媒体一遍遍自揭身世的访问中,如她自己所言,“被家暴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也许正是那千百次剖白的淘洗,令她最终交出的作品,在题材上显得“避重就轻”:她大可打造一个离家出走叛逆少女,邂逅花花世界的奇情成长记,或是迎上“东亚小孩原生家庭”的舆论东风,放大罪与罚之下的暴力阴影。
然而,没有《热辣滚烫》式逆袭复仇的超燃结局,也没有《好东西》中处处让人莞尔的诙谐过程,舒淇将《女孩》轻拿轻放,平静地落在“不懂爱的父母会对小孩造成多大的伤害”上,与其说这是一部文艺剧情片或半自传电影,它更像导演以“过来人”身份,投向主人公林小丽(白小樱饰,取自舒淇原名林立慧),或是“女孩”时期自己的深情回眸,有散文诗般的温柔细腻,也有自言自语的破碎踟蹰,因其既真且拙,方见一片冰心。
撰文 | 一把青
细节推动情节
围绕青少年成长与家庭羁绊、自传色彩浓郁的作品,远有侯孝贤《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一》;近有《阳光普照》的两兄弟,还有讲述台中家庭式理发店的《本日公休》、台南餐厅单亲妈妈与三个女儿的《孤味》,向来是台湾电影脉络中一张王牌。不同于这些摄影机背后、文本出发的创作者,从镁光灯焦点处走来的演员舒淇,经历过华语电影黄金时代,她拥有最佳的职业修养,擅长通过细节勾连起画面,继而氤氲开场景与情绪,这是当好“说故事的人”的切入口,在她不少谈及童年的采访中都可见一斑。
被问起小时候最害怕什么?她不假思索回答,是窗外摩托车的声音:要辨别那是不是爸爸的车,再从引擎的“突突”声连贯与否,分析他今天喝醉了没有,醉了难免要遭毒打,所以就要躲到塑胶衣橱中,再轻轻拉上布帘的拉链。

[加西网正招聘多名全职sales 待遇优]
| 分享: |
| 注: | 在此页阅读全文 |
| 延伸阅读 |
 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歌词赏析 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歌词赏析 |
推荐:
 舒淇《女孩》:写给青春的散文诗
舒淇《女孩》:写给青春的散文诗